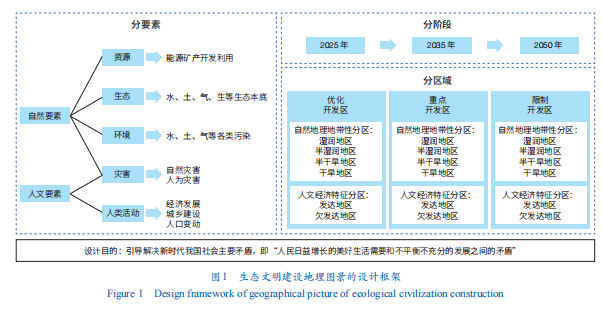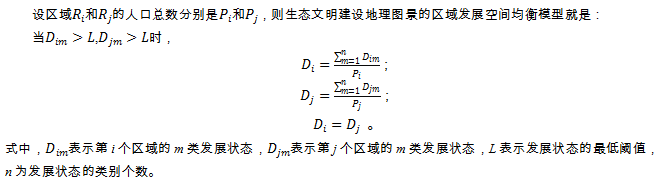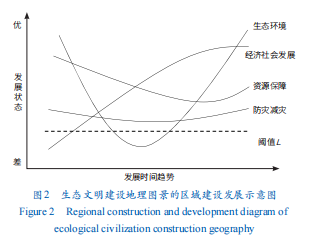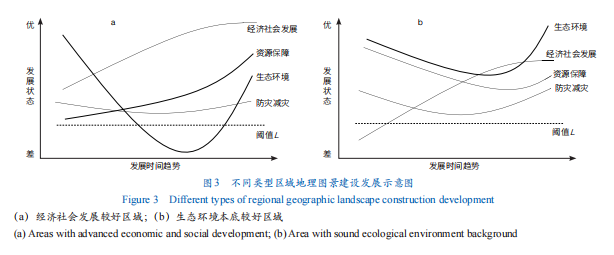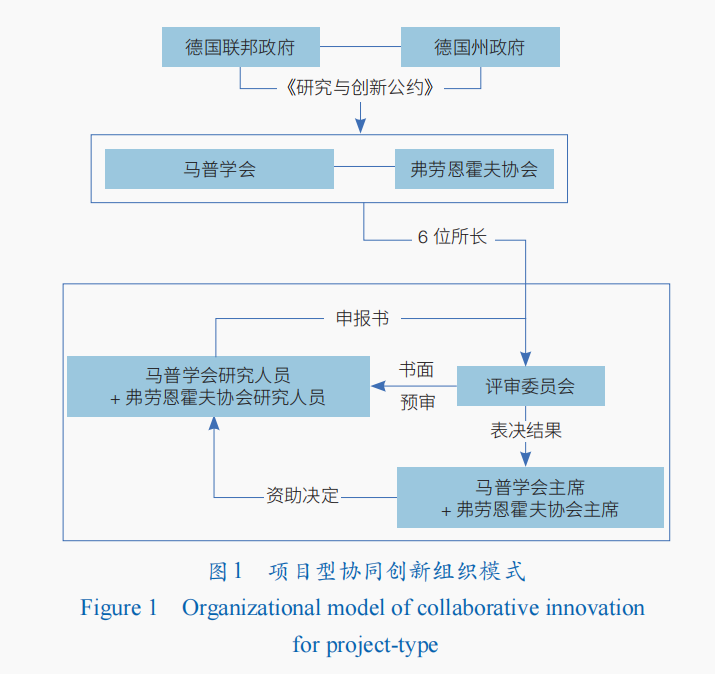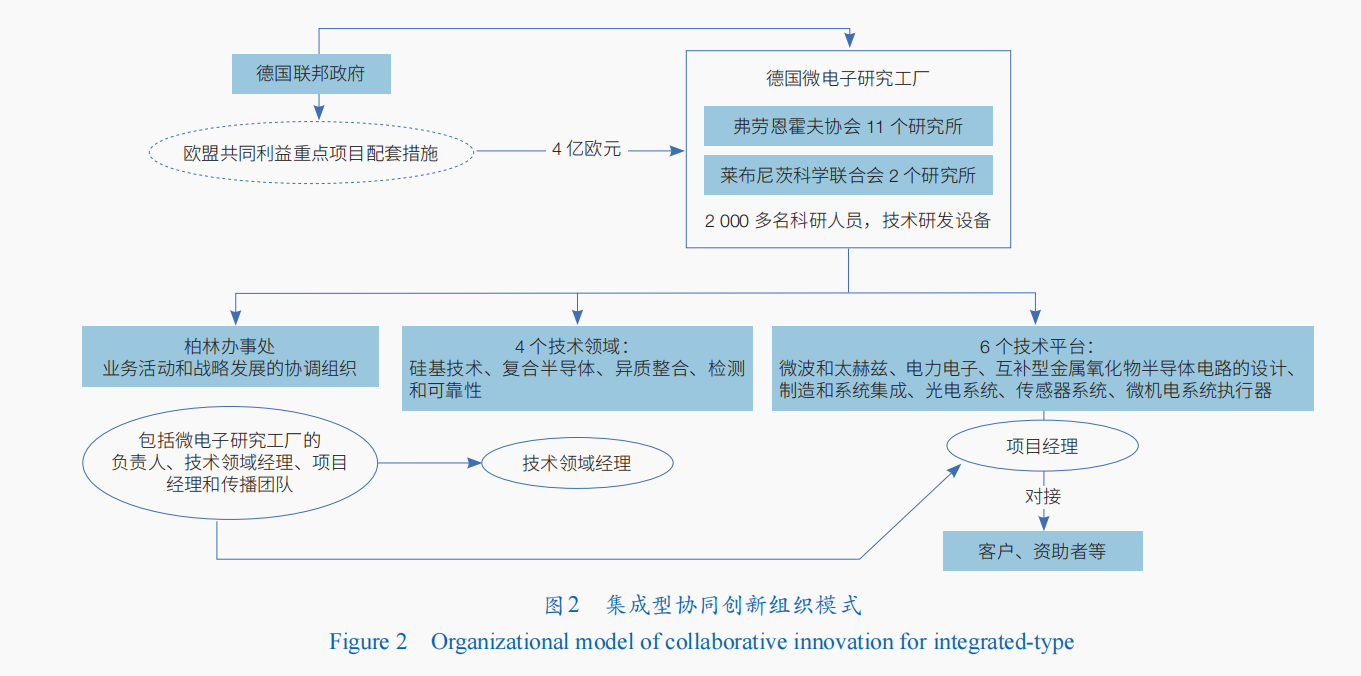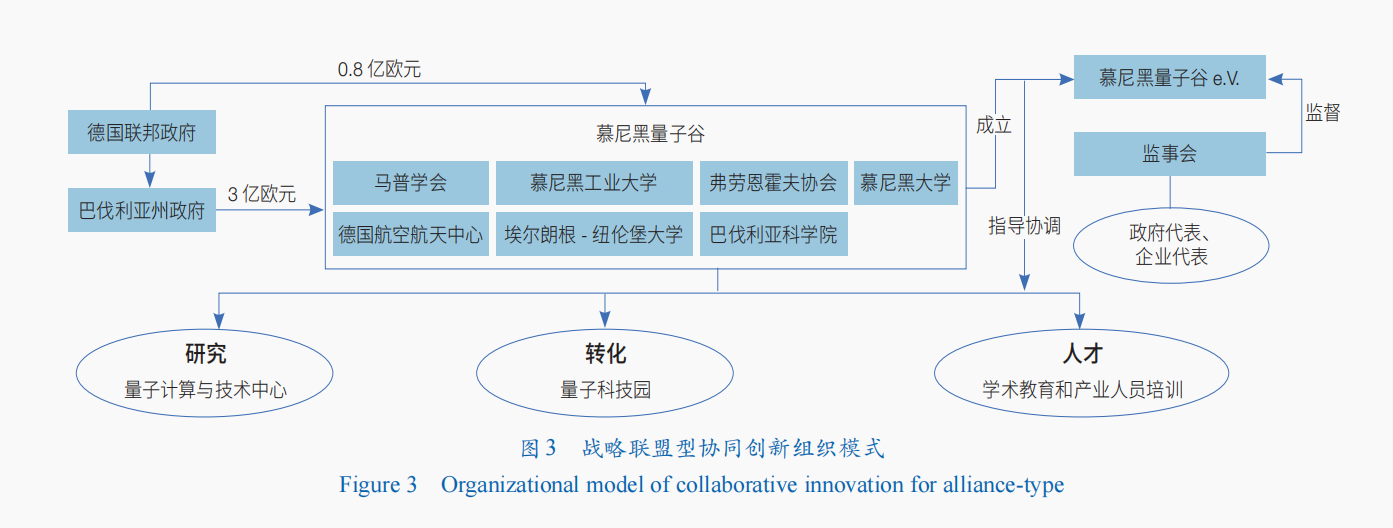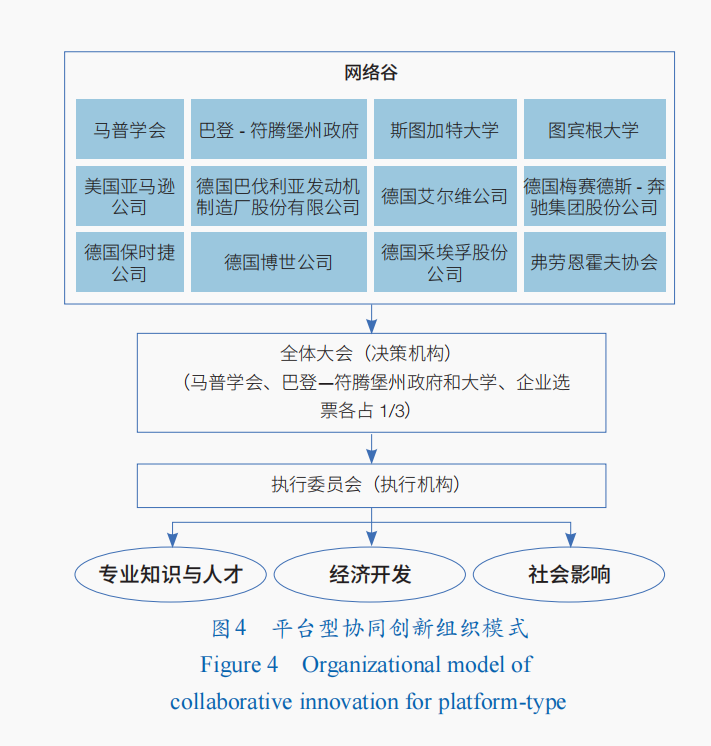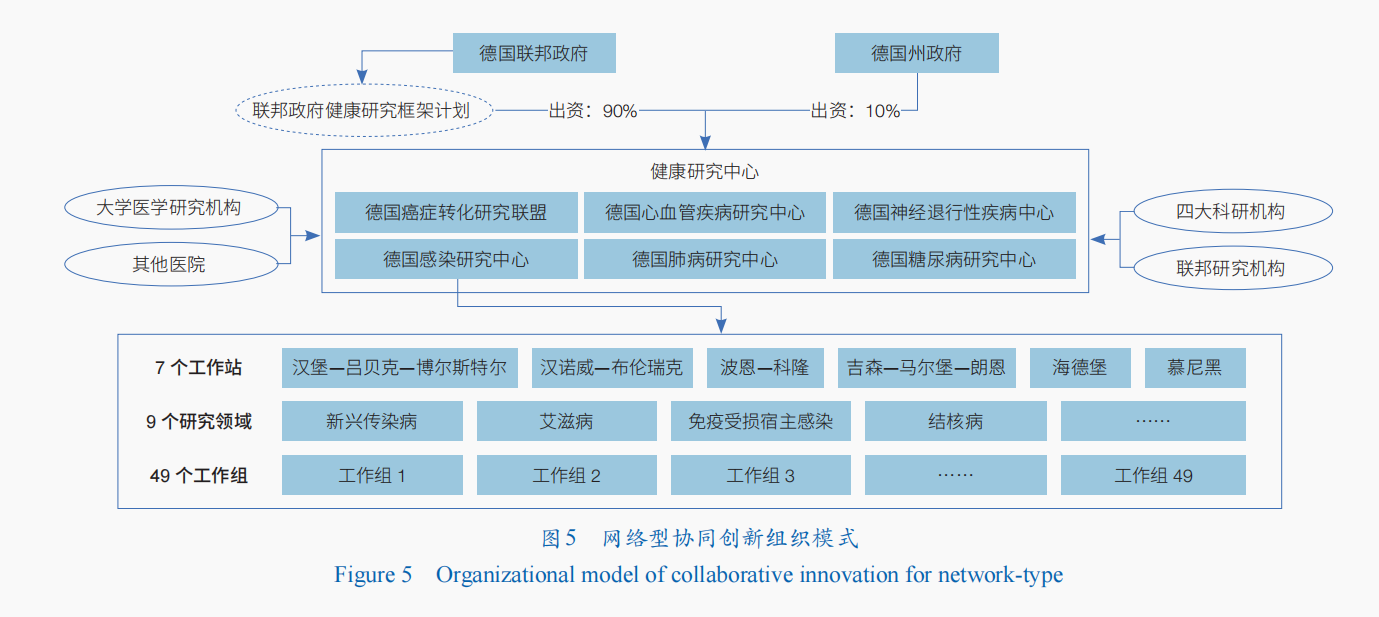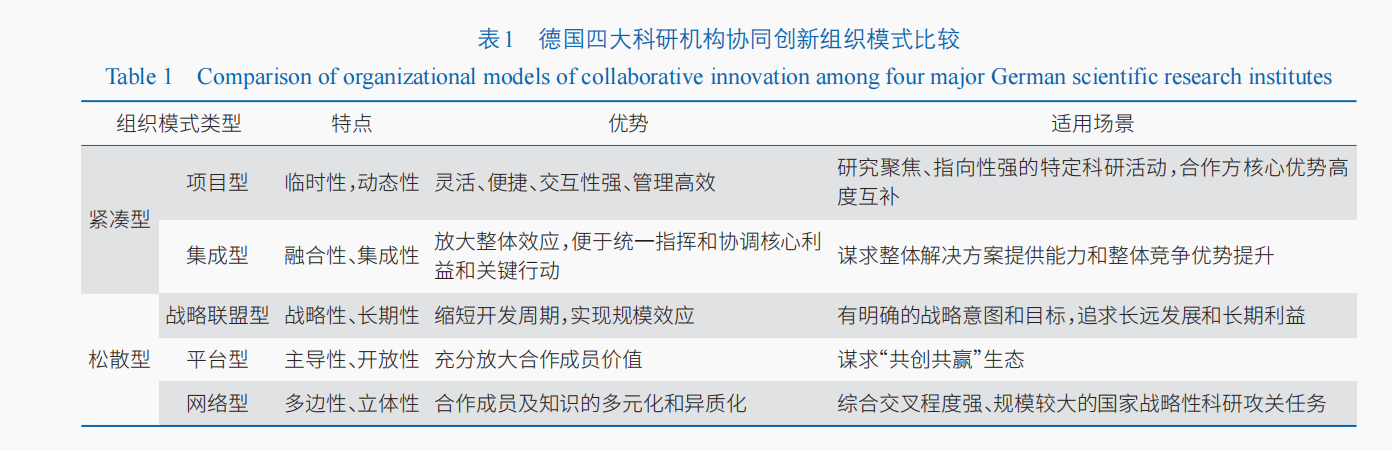要害詞:趙樹理 重讀經典 張莉 《掛號》

《掛號》,趙樹理著,工人出書社1950年版

《說說唱唱》,李伯釗、趙樹理任主編,1950年1月在北京創刊,1955年3月復刊,共出刊63期。
《掛號》是趙樹理寫于1950年的有名短篇小說。會商這部作品,不得不談到八十年月廣為傳播的有名唱段《燕燕作媒》,它取自滬劇《羅漢錢》,曾取得第一屆全國戲曲不雅摩表演年夜會腳本獎和表演獎。而不為人知的是,《羅漢錢》即是由趙樹理的《掛號》改編而來。
《掛號》旨在宣揚新中國第一部《婚姻法》。這部轉變每個中國人生涯的法典公佈于1950年5月1日。“1950年炎天,恰是鼎力宣揚婚姻法的時辰,刊物急需求頒發反應這一題材的作品,但編纂部卻沒有這方面的稿子。編委會決議本身脫手寫。誰寫呢?推來推往,最后這一義務就落到了老趙頭上。這是命題作文章,也叫做‘趕義務’,普通的說來是‘趕’不出什么好作品來的。老趙卻很快‘趕’出了一篇評書體的短篇小說《掛號》。”[1]
《掛號》完成于1950年6月5日,頒發在《說說唱唱》1950年6期,約有14000字。故事所寫的是1950年,在山西東王莊,母親小飛娥有意間發明女兒艾艾的羅漢錢,回想起20年前本身與保安相戀,后來自願嫁給張木工,從此婚姻生涯陷于暴力和膽怯之中的經過的事況,煩惱女兒重蹈覆轍,小飛蛾謝絕了伐柯人五嬸的說親。艾艾由於與小晚往來被村人視為“名聲不正”,燕燕上門為艾艾做媒,小飛娥批准了孩子們的親事。但村公所仍然不準掛號。村里的青年小進和燕燕的愛情也遭到障礙。兩個月后,《婚姻法》公佈,艾艾和小晚掛號并被視為模范婚姻,燕燕和小進后來也美滿聯合。
《掛號》完整可以說是一個新中國故事,一頒發便惹起文藝界激烈反應,很快被改編為戲曲《羅漢錢》,以處所戲情勢演出(滬劇只是此中的一種)。讀《掛號》,會很天然地想到趙樹理的成名作《小二黑成婚》,現實上,研討者們后來將這兩部作品稱為姊妹篇。兩部作品雷同之處在于有配合的主題——都是年青人沖破重重阻力尋覓婚姻不受拘束。但分歧也很顯明:《小二黑成婚》的故事產生1943年的束縛區,那時還沒有《婚姻法》;《掛號》產生在七年后,新中國曾經成立,《婚姻法》方才公佈。于是,異樣的婚姻不受拘束主題,異樣書寫母女兩代的關系,比擬而言,《掛號》的調性更為開闊爽朗歡樂,年青人也變得更為英勇和自動。
和《小二黑成婚》共享一個故事核,《掛號》是若何創新、發展出新穎枝椏而令人膾炙人口的?與《小二黑成婚》比擬,《掛號》中的女性抽像與年青人抽像塑造方面有何明顯分歧;在移風易俗的過程中,趙樹理若何在國度話語與女性本身氣力之間尋覓到他的論述戰略?這是本論文感愛好之處,也是重讀目標地點。
“人是苦蟲”?小飛蛾與她的“遲緩覺悟”
《掛號》頒發時被標誌為“評書”。開首便以平話生齒吻呈現:“諸位伴侶們:明天讓我來說個新故事。這個故事標題叫《掛號》,要從一個羅漢錢說起。”[2]故事分紅四部門:一、羅漢錢;二、眼光;三、不準掛號;四、誰該檢查。
全體而言,小說的四部門構造嚴謹,對應傳統故事“起、承、轉、合”。固然四部門字數平衡,小說的重點也講的是年青一代若何戰勝艱苦往掛號,但小說中讓人最印象深入的仍是“羅漢錢”,也是新故事產生的佈景,母親小飛蛾的舊故事。
三十年前,作為新媳婦的小飛蛾姣美而活躍,但村里人漸漸傳來了她的閑話,清楚到她以前的相好叫保安,張木工也發明,小飛蛾身上的羅漢錢是二人定情的信物。在最後,張木工并沒有要用武力克服小飛蛾,他只是把不滿告知了母親,母親則教唆他:“快打吧!現在打還打得過去!要打就打她個夠受!輕來輕往不抵事!”[3]受鼓動的兒子頓時脫手,“他拉了一根鐵火柱正要走,他媽一把拉住他說:‘快丟手!不克不及使這個!細家伙打得疼,又不傷骨頭,頂好是用小鋸子上的梁!’”[4]
“張木工打媳婦”是羅漢錢里很是主要的場景。每一位讀者城市對張木工若何“經驗”小飛蛾的片段難以忘卻:
她是個嬌閨女,歷來沒有挨過誰一下打,才挨了一下,痛得她叫了一聲低下頭往摸腿,又被張木工捉住她的頭發,把她按在床邊上,拉下褲子來“披、披、披”連續打了好幾十下。她起先還怕招得人來看笑話,憋住氣不想哭,后來其實支不住了,只顧喘息,想哭也哭不下去,比及張木工打得沒了勁扔下家伙走出往,她感到滿身的筋往一處抽,喘了半天賦哭了一聲就又壓住了氣,頭上的汗,把頭發濕得跟在熱湯里撈出來的一樣,就如許喘一陣哭一聲喘一陣哭一聲,差未幾有一頓飯功夫哭聲才連起來。……小飛蛾哭了一陣以后,屁股蛋疼得似乎誰用錐子剜,摸了一摸滿手血,咬著牙兜起交流褲子,站也站不住。[5]
固然講故事人和聽眾/讀者一路不雅看張木工打人場景,但小說所聚焦和轉達的倒是被打者的感觸感染、痛苦悲傷和辱沒。而如許的痛苦悲傷和辱沒使活躍的小飛蛾像換了小我一樣,從今生活在膽怯中。
從挨打那天起,她看見張木工好象看見了狼,沒有措辭先發抖。張木工也莫想看上她一個笑容——每次回來,從門外看見她仍是活人,一進門就釀成逝世人了。有一次,一個雞要下蛋,沒有回窩里往,小飛蛾正在院里攆,張木工從外邊回來,看見她那神情,真有點像在戲臺上系著白羅裙唱白娘娘的阿誰小飛蛾,可是小飛蛾一看見他,就連雞也不攆了,趕忙規行矩步走回屋子里往。張木工生了氣,攆到屋子里跟她說:“人說你是‘小飛蛾’,怎么一見了我就把你那同黨耷拉上去了?我是狼?”“呱”一個耳刮子。小飛蛾由於不愿多挨耳刮子,也想在張木工眼前裝個笑容,惋惜是非論怎么裝也裝得不象,還不如不裝。張木工看不上活躍的小飛蛾,覺著家里沒了趣,以后到外邊做活,一年半載不回家,途經家門口也不愿出來,傳聞在裡面找了好幾個相好的。[6]
毆打使她轉變性格,活躍性情就此消散。對于小飛蛾而言,已經愛上過他人曾經成為她的原罪。小說動情地書寫了小飛蛾遭遇家庭暴力后所感觸感染到的孤單、凄惶和無處依回。“小飛蛾離外家固然不遠,可是有嫌疑,往不得;外家爹媽傳聞閨女丟了丑;也沒有臉來探望。如許一來,全世界上再沒有一小我跟小飛蛾是一勢了。”[7]沒有人輔助小飛蛾,包含同為女性的婆婆。現實上,在張木工家暴行動的背后,婆婆起了火上加油的感化。
他媽把他叫到背後里,罵了他一頓“沒骨頭”,罵而已又勸他說:“人是苦蟲!痛痛打一頓就悔改來了!舍不得了不起……”他受過了這頓經驗以后,就好好留意找小飛蛾的茬子。[8]
“人是苦蟲”,是一種處所方言。“苦蟲:意謂人道賤,少不了都要禁受磨難。舊時官府罵人的話,謂人是賤骨頭,不鞭撻就不會供認。”[9]“人是苦蟲”這句話在《掛號》里呈現了兩次,一次是後面張木工母親鼓動他往打小飛蛾時,而另一次則是五嬸往說媒,被問起艾艾是不是還能改時,五嬸答覆說:“改得了!人是苦蟲,痛痛打一頓以后就沒有事了!”[10]對方又說:“生就的骨頭,哪里打得過去?”[11]五嬸則說:“打得過去,打得過去”!小飛蛾那時辰,還不是張木工一頓鋸梁子打過去的?”[12]某種意義上,就這部小說而言,“人是苦蟲”中的“苦蟲”特指女人,指的是那些有過愛情史或許婚前有過相好的女人,而教導她們的方法即是“打”,——“人是苦蟲”有如password,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像空氣一樣對女性的輕視與恥辱,也會天然聯想到那時諸多鄉村女性在婚內被不竭毆打、改革的故事,但在那時,很少有人認識到毆打自己的題目。
1950年的小飛蛾再次聽到五嬸這句“人是苦蟲”時,表達了“不服”。“她想:‘莫非這挨打也得一輩傳一輩嗎?往你媽的!我的閨女用不著請你管束!’”[13]這是作為母親的小飛蛾的對抗和她的不平服,也是對像空氣一樣的舊習氣和舊風俗說不。現實上,即便昔時被張木工毆打,小飛蛾也并沒有真的被“改革”:
小飛蛾只好一面服侍婆婆,一面偷偷地玩她阿誰羅漢錢。她天天早晨打發婆婆睡了覺,回到本身屋子里打開門,把羅漢錢拿出來看了又看,有時辰對著羅漢錢靜靜說:“羅漢錢!要命也是你,保命也是你!人家打逝世我我也不舍你,咱倆逝世活在一路!”她有時辰變得跟小孩子一樣,把羅漢錢熱得手心里,貼到臉上,按到胸上,銜到口里……除了張木工回家來那稀有的幾天以外,天天早晨她都是離了羅漢錢睡不著覺,直到生了艾艾,才把它存到首飾匣子里。[14]
孫先科在剖析小飛蛾這一抽像時以為:“小飛蛾固然被張木工用鋸梁子懲戒與規訓,但小飛蛾并沒有完整被改革。張木工可以使她怕,但不克不及使她愛,張木工不在場時,她的神情依然像‘在戲臺上穿戴白羅裙唱白娘子的阿誰小飛蛾’,……或許說張木工只懲戒了她的皮肉,并沒有改革她的心氣;張木工嚇破了她的膽,并未虐殺她的精力,她依然是阿誰賭氣勃勃的小飛蛾。”[15]也是以,他將小飛蛾稱之為有烈性氣質的“蛾式女人”,這一剖析實為精當。
恰是由於“不服”的性情,小飛蛾面臨本身過往和女兒的親事時,多了一些思慮。在最後看到女兒手里的“羅漢錢”時,她并不克不及判定這是件功德仍是一件好事,但聽到五嬸說“人是苦蟲”時,她認識到女兒將來應當如何生涯的題目:
五嬸那兩句話似乎戳破了她的舊傷口,新事往事,想起來再也放不下。她想:“我娘兒們的命運為什么這多一樣呢?現在不了解是什么鬼跟上了我,叫我用一只戒指換了個羅漢錢,害得后來被人家打了個半逝世,直到此刻還跟監犯一樣,一出門人家就得在后邊押送著。現在這事又出在我的艾艾身上了。真是冤孽:我會干這沒前程事,你偏也會!從這前半截工作看起來,娘兒們好象鉆在一個圈子里,傻孩子呀!這個圈子,你媽半輩子沒有得跳出往,莫非你就也跳不出往了嗎?”[16]
看到女兒將來的生涯隱患,母親能否還請求女兒走本身的老路?小飛蛾在這里浮現了她的主體性。現實上,這位母親也認識到,她已經的遭際也不只僅是她一小我的遭際:
她又前前后后想了一下:非論是和她年事差未幾的姊妹們,非論是才出了閣的姑娘們,凡有像羅漢錢這一類行動的,就沒有一個不挨打——婆婆打,丈夫打,尋自殺的,守活寡的……“歸正挨打的根兒曾經扎下了,賤骨頭!不爭氣!許就許了吧!非論嫁給誰還不是一樣挨打?”[17]
既然大師都有如許的遭際,就順著命運嗎?當然不。小飛蛾不是那樣唾面自乾的女性。一如小說中所說:
腦筋如果簡略叫點,打下這么個主張也就算了,可是她的腦筋偏不那么簡略,閉上了眼睛,就又想起張木工打她那時辰那股牛勁:瞪起那兩只吃人的眼睛,用盡他那一身力量,滿把子揪住頭發往那床沿上“撲差”一近,跟打騾子一樣連續打幾十下也不讓人喘口吻……“媽呀!怕煞人了!二十年來,幾時想起來都是渾身打發抖!不可!我的艾艾哪里受得住這個?”[18]
這是屬于母親的遲緩而果斷的覺悟,——再也不讓女兒走老路,這位母親要放女兒到光亮中往,換句話說,固然這是屬于母親的舊故事、艾艾故事產生的前史,可是,在這個舊故事里曾經包括了新故事的曙光,這也為艾艾和小晚的不受拘束聯合做了展墊。
當然,小說也還有伏筆。固然村莊里有很多女人被打過,但也并不是一切女人有小飛蛾的覺醒。一如張木工的母親,恰是她攛掇兒子往打兒媳婦的,不只僅攛掇,並且還告知他哪個打得最疼:“他媽為什么了解這家伙好打人呢?本來他媽昔時年青時辰也有過小飛蛾跟保安那些事,后來是被老木工用這家具打過去的。”[19]並且在兒媳婦挨打之后,并不表現同情:“一家住一院,外邊人聽不見,張木工打而已早已走了,婆婆連看也不來看,遠遠地在北房里喊:‘還哭什么?看多么排場?多么有面子?’”[20]這種享福的媳婦后來又成為嚴格管束媳婦的婆婆類型,在趙樹理小說是一個系列,她們保守而固執,是鄉村家庭中特有的人物系列。這也恰是《掛號》中艾艾的故事產生的泥土和佈景,蘇醒的人是多數。作為小說家,趙樹理以小飛蛾際遇動身,所要講述的是作為泥土和空氣的對女性戕害的舊風俗。
在婦女抽像塑造中,趙樹理實在并沒有塑造束縛區文藝中一種廣泛而主要的人物抽像,如喜兒(《白毛女》)、燕燕(《赤葉河》)、趙巧兒(《趙巧兒》)、藍妮(《趕車傳》)等遭到田主階層危害、欺侮的女性抽像。這也恰是趙樹理與其他束縛區作家的分歧,一如黃修己所說,“這闡明趙樹理塑造這個抽像系列,重要不在于揭穿田主階層的罪行,而在于表達他對改造鄉村封建陋習的激烈愿看,依靠著他對婦女束縛的幻想。”[21]
趙樹理小說重要是對鄉村風氣的批評,恰是如許的批評使小飛蛾作為汗青中心物取得了她的主體性:她是新舊故事的連接者,舊的故事的受益者,而在新故事里,她則要做一個新的晚輩和母親。小飛蛾不是靠別人或外力的啟示,而是從本身經歷動身的覺悟,它是趙樹理小說中少有的有主體認識的母親抽像。
欲海掙扎:三仙姑與小飛蛾人生的裂變
《小二黑成婚》在趙樹理創作中有著很是主要的位置。“這篇成名作以其塑造最主要的人物抽像,觸及最常常呈現的題目,而確立了它在全部作家創作中的宗子位置。鄉村社會的奇特看法,在《小二黑成婚》中曾經基礎上表現出來了。”[22]確乎這般。《小二黑成婚》里包括了趙樹理小說的諸多創作母題。而把《掛號》和《小二黑成婚》兩絕對照,也很不難發明它們的共通性:仍然寫年青一輩若何衝破阻攔完成婚姻不受拘束;人物設定也是附近的,包含父一輩的有些老頭腦和小字輩的艾艾、燕燕、小晚、小進。甚至構造上也很是附近。在寫掛號和若何掛號時,作家先蕩開一筆寫“羅漢錢”,一如寫小二黑成婚時作家先寫三仙姑和二諸葛以及金旺兄弟等等,被稱為“峰回路轉式”的構造。但《掛號》和《小二黑成婚》的小說調性有顯明差別,《小二黑成婚》面臨的是革命權勢、是黑惡權勢,而艾艾、小晚所面臨的則是新社會,是新社會里的權要主義。也是以,《掛號》中的年青人盡管碰到了波折,但卻讓人感觸感染到一種盼望和氣力在號召。兩部小說中,晚輩的氣力也在產生變更。《小二黑成婚》里,三仙姑和二諸葛是主要的阻攔氣力,可是在《掛號》中,父輩并不是最年夜的阻攔氣力,甚至他們中一些人在親情的感化下開端支撐年青人自立婚姻。
當然,這兩部小說都進獻了深有光澤的人物,《小二黑成婚》里是三仙姑,《掛號》里則是小飛蛾。盡管她們并不是小說中的主人公,也不是作家所要歌唱的對象,可是,她們各自擁有屬于遠高于新一代/新人的文學光線。
某種意義上,三仙姑和小飛蛾是有著雷同處境的人:兩位女性都是姣美媳婦,年青時都很吸引同村青年的眼光,別的,她們都有著不幸福的婚姻,同時,也都各有對抗性。趙樹理若何講述這兩個女性的欲看、若何懂得這兩位女性的對抗,實在背后代表了作家對女生命運的分歧視點。
《小二黑成婚》以漫畫式的方法記載了三仙姑這一類的鄉村女性。她長得都雅,對婚姻和丈夫并不滿足。而婚姻詳細若何不幸,小說并沒有正面描述。在教學提到她的丈夫于福時,只是說,他只會在地里逝世受。
三仙姑下神,足足有三十年了。那時三仙姑才十五歲,方才嫁給于福,是前后莊上第一個姣美媳婦。于福是個誠實后生,未幾說一句話,只會在地里逝世受。于福的娘早逝世了,只要個爹,父子兩個一上了地,家里只留下新媳婦一小我。村里的年青人們感到著新媳婦太孤獨,就漸漸主動地來跟新媳婦做伴,不幾天就聚集了一年夜群,天天嘻嘻哈哈,非常紅火。于福他爹看見不像個樣子,有一天發了性格,痛罵一頓,固然把外人蓋住了,新媳婦卻跟他鬧起來。新媳婦哭了一天一夜,頭也不梳,臉也不洗,飯也不吃,躺在炕上,誰也叫不起來,父子兩個沒了措施。鄰家有個妻子替她請了一個神婆子,在她家下了一回神,說是三仙姑跟上她了,她也哼哼唧唧自稱吾神長吾神短,從此以后每月初一、十五就下起神來,他人也給她燒起噴鼻來求財問病,三仙姑的噴鼻案便從此設起來了。[23]
“跳年夜神”是三仙姑處理窘境的一種手腕,某種意義上,也是她隱秘欲看宣泄的出口,小說里,有著茂盛欲看的三共享會議室仙姑是被譏笑的,起首是對她服飾的譏笑。
青年們到三仙姑那里往,要說是往問神,還不如說是往看圣像。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師的苦衷,衣服穿得更換新的資料鮮,頭發梳得更滑膩,首飾擦得更明,官粉搽得更勻,不由青年們不隨著她轉來轉往。[24]
論述人用了“更換新的資料鮮”“更滑膩”“更明”“更勻”,來直接描寫三仙姑的自動、盼望及矯枉過正。與三十年前的抑制比擬,在寫三仙姑三十年后的穿戴時,批駁和指責則更不遮蔽。小說中寫到三十年后的漢子們都長了胡子不再往三仙姑家跑,但“三仙姑卻和大師分歧,固然曾經四十五歲,卻偏心當個老來俏,小鞋上仍要繡花,褲腿上仍要鑲邊,頂門上的頭發脫光了,用黑手帕蓋起來,只惋惜官粉涂不服臉上的皺紋,看起來似乎驢糞蛋高低上了霜。”[25]“偏心當個老來俏”“小鞋上仍要繡花“ 褲腿上仍要鑲邊”,再加上后面的比方“驢糞蛋高低上了霜”,顯然都是極盡嘲諷之意。或許可以說,整部小說中,作為異類的三仙姑是一位被譏笑和譏諷的對象,簡直看不到作者對她的同情。
同時,小說也直白地寫出了三仙姑分歧意小芹和小二黑成婚的緣由,是由於她與女兒的爭風吃醋:“她跟小芹雖是母女,近幾年來卻不合錯誤勁。三仙姑愛的是青年們,青年們愛的是小芹。小二黑這個孩子,在三仙姑看來似乎鮮果,惋惜多一個小芹,就沒了本身的份兒。……開罷斗爭會以后,飛短流長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不受拘束成婚,她想要真是那樣的話,以后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克不及了,那是多么惋惜的事,是以托店主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。”[26]這是進木三分的書寫,三仙姑的不幸里,包含欲看無法知足,也包含人道深條理的母女相嫉、母女相妒。《小二黑成婚》尖利書寫了三仙姑身上性欲的蓬勃與母性的匱乏。
小飛蛾也是性命能量茂盛的女性。“本來這處所一個梆子梨園里有個著名的武旦,身體不很高,那時辰也不外二十明年,一進場,抬手動腳都有戲,眉毛眼睛城市措辭。唱《金山寺》她裝白娘娘,跑起來白羅裙滿臺飛,一小我撐滿臺,好象一只蠶蛾兒,人都叫她‘小飛蛾’。”[27]“白娘娘”“蠶蛾兒”的表述,都意味著這個女性別有一種性命力。在講述小飛蛾的不幸時,小說家看到了這位女性的不馴,即便是沒有《婚姻法》的加持,她在心坎里也不愿意讓孩子往走本身的悲傷路,是以激烈表達了對舊習氣的對抗。這意味著,在女性束縛題目和若何懂得女性的題目上,七年前的趙樹理和七年后的趙樹剃頭生了變更,這也讓人想到,“非論趙樹理是如何一個鄉土作家,非論他如何站在鄉土平易近間和農人的態度上,但是,他的心坎依然顛末了古代的浸禮和反動的風暴。他和年夜部門中國古代作家一樣,深深的卷進了古代世界的汗青潮水和漩渦之中。”[28]
兩位母親都有面臨女兒親事時的改變。三仙姑的立場改變是由於在區長辦公院子里被圍不雅。
區長端詳了她一眼道:“你就是小芹的娘呀?起來!不要裝神作鬼!我什么都明白!起來!”三仙姑站起來了。區長問:“你本年多年夜歲數?”三仙姑說:“四十五。”區長說:“你本身了解一下狀況你裝扮得像小我不像?”門邊站著老鄉一個十明年的小閨女嘻嘻嘻笑了。路況員說:“到外邊耍!”小閨女跑了。區長問:“你會下神是不是?”三仙姑不敢答話。區長問:“你給你閨女找了個婆家?”三仙姑答:“找下了!”問:“使了幾多錢?”答:“三千五!”問:“還有些什么?”答:“有些首飾布疋!”問:“跟你閨女磋商過沒有?”答:“沒有!”問:“你閨女愿意不愿意?”答:“不了解!”區長道:“我給你叫來你親身問問她!”又向路況員道:“往叫于小芹!”
適才跑出往阿誰小閨女,跑到外邊一宣揚,說有個進行訴訟的妻子,四十五了,擦著粉,穿戴花鞋。附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,擠了半院,唧唧噥噥說:“了解一下狀況!四十五了!”“看那褲腿!”“看那鞋!”三仙姑半輩子沒有酡顏過,偏這會兒撐不住氣了,一道道熱汗在臉下流。路況員領著小芹來了,居心說:“看什么?人家也是小我吧,沒有見過?讓開路!”一伙女人們哈哈年夜笑。
把小芹叫來,區長說:“你問問你閨女愿意不愿意!”三仙姑只聞聲院里人說:“四十五”“穿花鞋”,羞得只顧擦汗,再也開不得口。院里的人們突然又轉了話頭,都說“那是人家的閨女”“閨女不如娘會裝扮”,也有人說“傳聞還會下神”,偏又有個了解內情的斷斷續續講“米爛了”的故事;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逝世。[29]
區長的壓力使三仙姑不得分歧意小二黑和小芹的親事。而她之所以要轉變穿著方法,也是由於別人的見解:“三仙姑那天在區上被一伙婦女圍住看了半天,其實覺著欠好意思,歸去對著鏡子研討了一下,真有點裝扮得不像話;又想到本身的女兒將近跟人成婚,本身還賣什么老來俏?這才下了個決計,把本身的裝扮從頂究竟換了一遍,弄得像個當晚輩人的樣子,把三十年來裝神弄鬼的那張噴鼻案也靜靜拆往。”[30]——三仙姑的改變是發自心坎的嗎?這是讓人猜忌的。一如研討者所言,他們“這些看似‘提高’的舉止,實在也是人生的不得已,他們要在社會急劇變更中保存起來保存上去便只能這般。或許這也是一種‘避實就虛’,由於他們不長短凡的超人,而是世俗中大都,是不得不跟上時期,而趁波逐浪的人。”[31]
諸多研討者都指出《小二黑成婚》中論述視角的決裂:“小二黑成婚的主題是歌唱不受拘束愛情,歌唱束縛區社會的提高。但從作品的現實描述看,它存在著兩個視角,看小二黑小芹的不受拘束愛情時,站在時期的高度,熱忱確定了他們的新思惟、新精力、新風采;看三仙姑這個不幸可厭的人物時,卻站在那時鄉村社會普通的、也是傳統品德的態度上,簡略地斥責她不象媳婦,不象晚輩。兩個視角并存,闡明作者那時倫理品德的牴觸。”[32]
七年之后,趙樹理為了共同婚姻法而創作出了《掛號》,某種水平上是對《小二黑成婚》故事的一次改寫。《掛號》中,小飛蛾不只斟酌到女兒不克不及走本身的悲傷路,也想到了和她有配合際遇的姐妹們。小飛蛾的改變,是情面和事理的同一。小飛蛾身上有樸實的母性,她愿意放兒女們到“光亮”中往。這是小飛蛾與三仙姑的主要分歧。當然,與三仙姑故事里的嘲諷比擬,小飛蛾故事部門也有著濃重的抒懷元素,不難惹起人的共情,這也是后來戲劇改編者對此一片斷不竭改編的主要緣由。仍然是母女,小飛蛾婚姻的不幸被作家深切注視,也被寄予深切關心。是以,“作品中固然也有兩個視角,兩種品德不雅念,但不是并存在作者一人身上。張家莊群眾是看小飛蛾,是站在傳統品德態度上,盡管他們代表著那時廣泛的品德認識,但在新品德不雅念沖擊下,已顯示出被代替的趨勢。作者看小飛蛾,是站在反傳統態度上,代表著與汗青成長同向的古代品德不雅念……”[33]
我認為,《掛號》中有著趙樹理對小飛蛾命運深具古代性別認識的書寫和注視,這是極為可貴的。不外,與《小二黑成婚》中三仙姑貫串全場分歧,小飛蛾只是在小說中的第一、二部門深具主體性,而在第三落第四章節,小飛蛾釀成了副角,釀成了怙恃輩中的一個,這與趙樹理小說“重事輕人”的作風有主要的關系。——作為小說家,趙樹理著重于處理題目、講述故事而不是書寫一小我的主體性若何確立。這也是《掛號》未能完全塑造出一個深具主體認識的鄉村母親抽像的緣由。
與“申明不正”:姐妹友誼與女性氣力
新中國《婚姻法》是對女性束縛有側重要的推進感化的法令。它的第一章第一條便開門見山:“廢止包攬逼迫、男尊女卑、疏忽後代好處的封建婚姻軌制。履行男女婚姻不受拘束、一夫一妻、男女權力同等、維護婦女和後代符合法規權益的新平易近主主義婚姻軌制。”而昔時《國民日報》社論則直接指出,這部法典深具女性束縛精力:“婚姻法的立法精力是要顛覆以男人為中間的‘夫權’安排。”
作為共同宣揚的小說,《掛號》美滿地轉達了《婚姻法》的條例:婚姻不受拘束、維護婦女權益。假如說“人是苦蟲”光鮮記載了舊故事里小飛蛾所遭到的辱沒,那么新故事所要面臨的則是那時鄉村對“申明不正”女性的輕視。申明不正/申明欠好/名聲不恰是附近的詞,在趙樹理小說中呈現的頻率并不低。《小二黑成婚》中,“名聲不正”呈現過一次,指的是三仙姑,“她本想早給小芹找個婆家發布門往,可是由於本身名聲不正,差未幾都不愿意跟她結親。”[34]在這個語義周遭的狀況里,“名聲不正”的評價與三仙姑是相符的,由於似乎她簡直是與良多漢子不清不楚。
七年后,當“名聲不正”/“申明不正”/“申明欠好”等相類的詞在《掛號》中成為高頻詞時,此中“申明不正”呈現了7次,而“申明欠好”呈現了3次。這些詞語呈現在分歧人物和分歧場景里,內涵推進著故工作節的成長。
“申明不正”第一次呈現是在艾艾、燕燕、小晚會商時,“小晚問燕燕,‘往年尾月你跟小進到村公所往寫證實信,村公所不給寫,是怎么說的?什么來由?’燕燕說:‘什么來由!還不是平易近事主任阿誰逝世頭腦作祟?人家說咱申明不正,除不給寫信,還叫我檢查哩!’”[35]這是逝世頭腦的村公所交流平易近事主任對燕燕的稱號。別的,在談到艾艾時,外人對她的評價是:“人樣兒滿說得曩昔,不外傳聞她申明不正!”[36]由此引出了需求對艾艾打一頓才幹矯正的聊天,這也是小飛蛾分歧意艾艾嫁給他人的主要緣由。
詳細什么是申明不正?小說頂用分歧人的口氣做過說明。在燕燕預計做小晚和艾艾的先容人時,王助理員并分歧意,緣由是“村里有陳述,說你的申明不正!”[37]于是三個青年人同問:“有什么證據?”王助理員則答覆說:“說你們早就有交往!”[38]在這里,掛號之前便早有交往即是“申明不正”的詳細行動。
平易近事主任是艾艾和小晚掛號成婚的障礙,在他那里,“申明不正”有兩個相反的估價:
有一次,他看見艾艾跟小晚拉手,他喃喃自語說:“壞透了!跟年青時辰的小飛蛾一個樣!”又一次,他在他姊姊家里給他的外甥提親提到了艾艾名下,他姊姊說:“不了解閨女怎么樣?”他說:“好閨女!跟年青時辰的小飛蛾一個樣!”這兩種評價,在他本身看起來并不牴觸:說“好”是指她長得好,說“壞”是指她的行動壞——他認為世界上的漢子接近女人就不是壞透了的行動。不外主任對于“身體”和“行動”還不是均勻主義見解:他認為“身體”是生成的,是什么就是什么,行動是可以跟著丈夫的意思轉變的,只需痛痛打一頓,說叫她變個什么樣就能釀成個什么樣。[39]
以上可以看出,從《小二黑成婚》到《掛號》,“申明不正”在兩部小說里的所指語義產生了變更——《掛號》里村莊里人們所謂的“名聲不正”,并不是真正的“名聲不正”,某種水平上,而是對那些性情活躍、不受拘束愛情的女性的臭名化稱呼。
《掛號》中貫串了女性們對“申明不正”的抗爭。從小飛蛾就開端了,在“眼光”部門,小飛蛾明白謝絕了五嬸提親;艾艾面臨婚姻題目時,有著強盛的主體性,果斷不跟除小晚以外的人成婚;而燕燕,不只僅不愿意屈服,還試圖輔助艾艾和小晚完成婚姻掛號。在得知艾艾和小晚的窘境后,小說有一段關于燕燕的描述:“燕燕驀地間挺起腰來,跟起誓一樣地說:‘我來當你們的先容人!我管跟你們兩端的年夜人們提這事!’”[40]這充足浮現了燕燕的英勇。現實上,在與“申明不正”做搏斗的經過歷程中,燕燕和艾艾并不蠻干,而是有具體的打算和設定:“艾艾又和燕燕打算了一下,見了誰該如何說見了誰該如何說,東院里五奶奶要給平易近事主任的外甥說成了又該如何頂。”[41]在掛號又一次碰到艱苦時,年青人想到了要相互輔助:“他們談到以后該怎么樣辦,燕燕依然幫著艾艾和小晚想措施,他們兩個也愿意幫著燕燕,叫她重跟小進好起來。用交際上的字眼說,也可以叫做‘訂下了合作公約’。”[42]
簡而言之,《掛號》固然寫的是年青人若何戰勝障礙往掛號,但實在內涵里寫的倒是女人們若何不平不撓地與“申明不正”做斗爭——整部小說,年青人都在和那種將愛情不受拘束視為“名聲不正”的逝世頭腦、權要主義搏斗。而正在束手無策之時,《婚姻法》有如東風一樣,一切水到渠成,——在“申明不正”的斗爭中,借助《婚姻法》的輔助,艾艾和小晚、燕燕和小進終極無情人終成家屬。當然,“掛號”并不是最后的終局,仍是要與權要主義與逝世頭腦表達了不滿,那是年青人另一種層面上的抗爭。
艾艾說:“大師不是都了解我的申明不正嗎?你們了解這怨誰?”有的說:“你說怨誰?”艾艾說:“怨誰?誰不叫我們兩小我緒婚就怨誰!你們大師想想:如果早一年結了婚,不是早就正了嗎?大師講起官話來,城市說:‘男女婚姻要自立’,你們說,我們村里誰自立過?說誠實話,有沒有一個不是怙恃主婚?”
……
區分委書記說;“你罵得對!我包管誰也不末路你們!群眾說你們申明不正,那是他們腦筋還有些封建思惟,以后要大師漸漸往失落。村平易近事主任由於想給他外甥先容,就不給你們寫先容信,那是他干預婚姻,中心國民當局公布了《婚姻法》以后,誰再有這種行動,是要送到法院判罪的。王助理員遲遲不發成婚證,那叫權要主義不願用頭腦!他本身這幾天正在區上檢查。中心國民當局的《婚姻法》公布以后,我們共產黨全黨包管履行,我們分委會也正在會商這事,明天就是為了彙集你們的看法來的!”[43]
區分委書記的講話恰是小說的點題,將一層層阻隔停止了剝離,年青人與“申明不正”的斗爭終極獲得成功。小說的開頭處,再一次與第一部門“羅漢錢”照顧:
開會以后,大師都說這種婚姻結得很好,都說:“兩小我以后必定很和睦,總不會像小飛蛾那時辰叫張木工打得個半逝世!”連一貫說人門風名不正的老頭子老太太,也有說好的了。
此日早晨,燕燕她媽的思惟就買通了,親身跟燕燕說叫她第二天跟小進到區上往掛號。[44]
新故事的完善開頭使《掛號》帶給人一種興高采烈。那是新瑜伽教室中國鄉村男女青年生涯的美妙圖景。“從《傷逝》描述子君、涓生這一對城市常識青年為不受拘束聯合停止斗爭而掉敗,到《小二黑成婚》中鄉村男女青年爭奪特性束縛取得成功,可以量出中國反動在20多年前所邁出的宏大程序。”[45]而假如說勝利的藝術作品是社會生涯的一面鏡子,那么,讀者從《掛號》可以看到新社會青年農人爭奪束縛的面影,看到新《婚姻法》給人們思惟精力面孔所帶來的新變更。
某種意義上,婚姻自立的主題、女性束縛的主題、新舊社會女生命運的對照主題,都在《小二黑成婚》里呈現了。但真正意義上的完成是在《掛號》里——小飛蛾的呈現是主要的,她并不是新人,但倒是令人倍感新穎,緣由在于她的覺悟和舉動,這也意味著新社會、新時期、新覺悟不只僅指的是新的年青人,也指他們的怙恃。
結語
讀《掛號》會想到趙樹理的講故事才能。盡管作品為宣揚而寫,可是趙樹理的故事自己卻有更為豐盛而廣大的向度。他的故事里總有著更為豐盛、復雜甚至牴觸的內核,這恰好也是他的故事被不竭解讀的魅力地點。當然讀這部小說也會想到張愛玲在《本身的文章》所說:“寫小說應該是個故事,讓故事本身往闡明,相比定的主題往編故事要好些。很多留到此刻的巨大作品,本來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留意,由於世易時移之后,本來的主題早已不使我們感到愛好,卻是隨時從故事自己發見了新的啟發,使那作品成為長生的。”[46]
良多年后,《婚姻法》曾經不用“宣揚”便深刻人心,但“掛號”的故事卻一向在被瀏覽。我們會超出《婚姻法》看到在逐步寬松的泥土里小飛蛾的自發和她身上所內蘊的性命能量。那是女性身上隱含的氣力。這氣力使女兒們不再走老路,這氣力在為后來的姐妹和女兒們盡能夠爭奪更年夜的能夠。——重視女性的能量并將其與作為國度話語的《婚姻法》聯合在一路,趙樹理的故事核里長出了新的活力勃勃的枝椏。
注釋:
[1]馬烽:《憶趙樹理同道》,《光亮日報》1978年10月15日。
[2][3][4][5][6][7][8][10][11][12][13][14][16][17][18][19][20]趙樹理:《掛號》,《趙樹理文集·第2卷》,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,第95頁、98頁、98頁、99頁、99頁、100頁、98頁、106頁、106頁、106頁、106頁、100頁、106頁、106-107頁、107頁、98頁、99頁、97頁、103頁、105-106頁、114頁、114頁、112頁、104頁、105頁、156頁、118-119頁、119-120頁。
[9]拜見百度百科:“人是苦蟲,不打不成”,網址: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人是苦蟲,不打不成/53798946?fr =aladdin。
[15]孫先科:《作家的“主體間性”與小說創作中的“間性抽像”——以趙樹理、孫犁的小說創作為例》,《河南年夜學學報(社會迷信版)》,2003年第1期。
[21][22]黃修己:《趙樹理創作抽像、母題和情節的組成》,《貴州社會迷信》1983年第3期。
[23][24][25][26][29][30][34]趙樹理:《小二黑成婚》,《趙樹理文集·第2卷》,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,第4頁、4頁、4頁、9頁、14-15頁、16頁、9頁。
[28]曠新年:《趙樹理的文學史意義》,《文藝實際與批駁》2004年第3期。
[31]董之林:《“工農兵小說”:淺顯外不雅下的生涯隱喻》,《長江學術》2013年第4期。
[32][33]陳興:《從三仙姑、小飛蛾人物塑造看趙樹理倫理品德不雅的成長》,《山西師年夜學報(社會迷信版)》1996年第23卷第3期。
[45]唐弢、嚴家炎主編:《中國古代文學史·第3卷》,國民文學出書社1980年版,第323頁。
[46]張愛玲:《本身的文章》,《張愛玲文集·第4卷》,金宏達、于青編,安徽文藝出書社1992年版,第175頁。